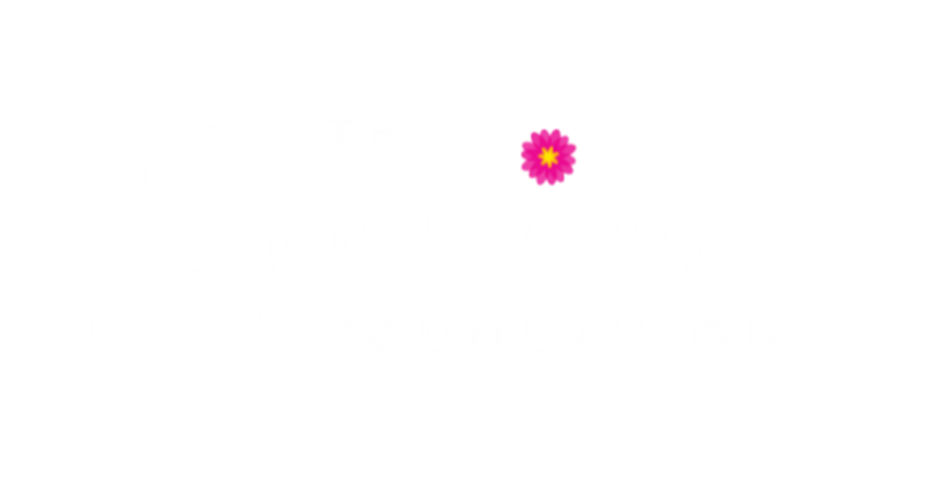NMOSD 故事:克里斯汀
2021 年 2 月 10 日
SRNA 的 GG deFiebre 加入了 Kristen Hewitt,SRNA 支持小组负责人和被诊断患有 NMOSD 的人。 克里斯汀首先描述了她的初始症状和她获得 NMOSD 诊断的过程。 她谈到了她接受的治疗和她在医疗系统中的经历。 克里斯汀讨论了 NMOSD 如何影响她的生活,包括持续的症状、工作生活和人际关系。 她谈到了她的恐惧和对未来的希望。 最后,克里斯汀谈到 NMOSD 如何影响她作为父母。
成绩单
简介: [00:00:00] NMOSD 基础知识是一个由 10 部分组成的教育播客系列,旨在分享有关视神经脊髓炎谱系障碍或 NMOSD 的知识,NMOSD 是一种罕见的复发性自身免疫性疾病,优先引起视神经和脊髓炎症。 NMOSD 播客系列的 ABC 由 SRNA、Siegel 罕见神经免疫协会主办,并与 NMO 的 Sumaira 基金会、Connor B. Judge 基金会和 Guthy Jackson 慈善基金会合作。 这个教育系列是通过 Viela Bio 的患者教育补助金实现的。
GG deFiebre: [00:00:59] 大家好,欢迎收看 NMOSD 播客系列的基础知识。 今天的播客是 NMOSD 故事:克里斯汀。 我叫 GG deFiebre,来自 Siegel Rare 神经免疫协会。 NMOSD 的基础知识是通过 Viela Bio 的患者教育补助金实现的。
[00:01:17] Viela Bio 致力于为患有各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和严重炎症性疾病的患者开发和商业化改变生命的新型药物。 他们的药物发现方法旨在为数以千计几乎没有或没有治疗选择的患者提供靶向治疗,以改善结果。 有关 Viela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vielabio.com 。
[00:01:39] 对于今天的播客,克里斯汀加入了我的行列,她被诊断出患有 NMOSD。
[00:01:45] 你好,非常感谢你今天和我聊聊你作为 NMO 人的故事和经历。 那么首先,您介意简单介绍一下您自己吗?
克里斯汀·休伊特: [00:01:57] 当然。 所以我叫克里斯汀。 我是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的一名 NMO 患者。 我是 SRNA 支持组组长,所以我在 NMO 社区中非常活跃。 我也是一个单身妈妈,我全职工作,然后我做了很多志愿者,所以我一直很忙。
GG deFiebre: [00:02:16] 是的,当然。 谢谢。 非常感谢您担任支持小组组长。 所以在考虑你的开始时,你知道,诊断,你的 NMO 发作,你在什么年龄开始出现症状,你有哪些最初的症状?
克里斯汀·休伊特: [00:02:34] 所以我的第一个已知症状,我说已知症状是因为在我得到诊断后,有点回顾我的医学,我的病史,还有另一起可能是 NMO 的事件,但在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我有 NMO,我们没有考虑过。 所以我最初的症状是,我必须解释的最好方式是当你在阳光下走到外面,然后你进入一个黑暗的房间,你会看到那些斑点和闪烁的灯光。 而我当时 24 岁。 我的工作让我搬到了一张可以看到窗外的办公桌前。
[00:03:07] 所以我认为这是因为我在工作时盯着窗外,然后在大楼周围走来走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取得了进展,变得更糟了。 最终,实际的景象开始完全消失,可以说,有点停电并靠近我。 这就是我 24 岁时的最初症状。
GG deFiebre: [00:03:29] 然后你说在那之前可能有一些事情。 什么,那些是什么,你认为最初可能也是 NMO 的那种经历是什么?
克里斯汀·休伊特: [00:03:38] 所以就在我有了我的儿子之后,也就是在视力问题出现前一年多一点,我出现了发作性睡病。 但我怀孕的时候真的很艰难,而且我一个人带新生儿,所以他们把这归因于生活环境。 但我现在知道,在获得 NMO 诊断后,这可能是 NMO 的症状。 所以对于那些,我,我记得只是失去了 30、45 分钟的时间块。 所以我会在看一个电视节目时正处于其中,然后突然醒来,那个节目已经结束,而我正在看另一个节目,或者正在看书,然后突然醒来,而且一直没有阅读一段时间。
所以这有点,那是在我的视力问题发生前一年发生的事件,我认为这可能也与 NMO 相关。
GG deFiebre: [00:04:35] 知道了。 然后,那么,那么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你知道,你说当你 24 岁的时候,你的视力开始下降,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你去过急诊室吗?
[00:04:44] 你看过你的初级保健医生或其他医生了吗? 只是告诉我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克里斯汀·休伊特: [00:04:50] 实际上我去看了我的验光师。 我认为这与视力有关。 我在电脑上工作。 就像我说的,我正在看着窗外,所以我想这可能与此有关。
[00:05:00] 所以我去看了我的验光师。 她进行了一些测试,基本上告诉我,“你需要立即就医。” 她拿起电话,拨通了眼科医生的电话。 眼科医生看到我,说,“你现在需要做核磁共振成像,”打电话给成像处,然后说,“你今天需要让她进来。” 所以基本上在一天之内,我就让我的验光师到我的眼科医生那里做了核磁共振成像。 然后它就停滞不前了。
[00:05:25] 我记得当时有点吓坏了。 我在医疗领域工作。 所以我有点利用它来发挥我的优势,我打电话给我并将成像结果传真给我。 我看了 MRI,它说有一个病变。 所以当然我有点吓坏了,因为我不知道我在看什么。
[00:05:45] 但是眼科医生不会给我看病。 最后他打电话说:“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 我不舒服。 我继续治疗你。 我想我想送你去……”所以我住在圣安东尼奥,所以我们这里有德克萨斯大学健康科学中心。 他就像,“那里有一位神经眼科老师,我想送你去那里。”
[00:06:07] 所以我打电话和他们约了时间。 这将是几周的时间。 在那段时间里,我的视力继续恶化。 我记得有一天电梯门在我面前关上了,因为我试图走进去,却没有看到它们离我的周边很近。
[00:06:22] 我拿起电话打了电话,有一天,神经眼科医生卡特医生在门诊前对我进行了检查,因为我的视力持续恶化。 那时,他查看了核磁共振结果,谈了一点病变,我们谈到它正在脱髓鞘。 如果你读过我的报告,放射科医生也指出它看起来不像多发性硬化症。 他说是脱髓鞘,其实不是,不是典型的多发性硬化脱髓鞘。
[00:06:58] 当时,因为我只有一个病灶,没有其他症状,他们基本上说以我的年龄,有可能是侥幸,他们会监视我。 他们确实经营了一些实验室。 我想他们当时做了 aquaporin-4 测试。 他们进行了测试以确保我没有任何可能导致病变或类似情况的感染。 他们还在我的核磁共振检查中发现我有 Chiari 畸形,所以我无法进行脊椎穿刺。
[00:07:27] 所以我无法进行脊椎穿刺并进行他们通常会做的额外测试。 所以我们决定监测一年或每年监测一次。 所以在那之后,我继续接受核磁共振检查,直到我第二次发作。 在这期间,我有过几次类似轻微的视神经炎发作,但只是眼睛疼痛。
[00:07:51] 我再也没有失去视力。 我从来没有遇到任何其他问题。 所以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我没有得到正式的诊断。 在那个特定的时间我没有达到任何诊断标准。 对于多发性硬化症和 NMO,您必须有一个以上的病变才能满足诊断标准。 因此,在我出现第二个损伤之前,我必须处于不确定状态三年。
GG deFiebre: [00:08:13] 知道了。 然后,在整个诊断过程中,他们是否也对水通道蛋白 4 或 MOG 抗体进行了任何血液测试?
克里斯汀·休伊特: [00:08:22] 所以,我不记得我们是否做了 aquaporin-4。 我知道我们没有做 MOG。 在我得到正式诊断大约一年后,我进行了 MOG 检测。 所以在第一次发作大约三年后,我的身体左侧开始出现刺痛和麻木感,尤其是我的脸。 我在脸上注意到了很多,因为当我触摸我的脸时,就像我坐在办公桌前,把手放在我的脸颊上,我能感觉到我的脸在睡觉的感觉,有点刺痛我的,我的脸。 它会从我的下巴开始,一直到我的额头。 那时,我的,我一直在跟踪我的神经眼科医生让我去做核磁共振检查,发现了另一个病变。 那时他正计划诊断我患有多发性硬化症,并打算给我开处方,这将是那些自我注射的疫苗之一。
[00:09:12] 我告诉他,我认为我做不到。 然后他把我送到了 UT 系统内的 MS 诊所。 当她看到我的图像和东西时,她看着它说,“我不认为你有 MS。 我想你有一个 NMO。 当时她确实派我去做水通道蛋白4测试,我是阴性的。
[00:09:31] 大约一年后,我们对 MOG 进行了测试。 当我进行初步诊断时,我不认为它可以在市场上买到,因为那是在 2017 年。
GG deFiebre: [00:09:41] 是的,这绝对是一个,你知道的,更新的,你知道的,测试,这是目前可供人们使用的。 所以我知道你说过你在两次发作之间等待这个诊断,对吧?
[00:09:52] 你正在等待第二次攻击来确认 NMO。 那你当时有没有诊断,或者他们给你解释了什么? 你知道吗,当时你的诊断可能是什么?
克里斯汀·休伊特: [00:10:04] 当时只是不明脱髓鞘。 所以他们没有给我任何形式的正式诊断。 如果你回去看我当时的病历,他们都说不明脱髓鞘。
GG deFiebre: [00:10:18] 知道了。 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是否给你做了大脑、脊髓和视神经的核磁共振成像,或者他们是否进行了除此之外的任何其他诊断测试?
克里斯汀·休伊特: [00:10:28] 我每年都会对我的大脑和视神经进行核磁共振检查。 当时他们做了,我还没有出现横贯性脊髓炎的症状。 当然,没有诊断,他们真的没有理由订购脊柱核磁共振成像。 所以我,他们每年都在做视神经、视神经和大脑核磁共振成像。
GG deFiebre: [00:10:49] 好的。 然后,你知道,在这段经历中,你对医疗系统有什么样的体验? 你的经历是怎样的?
克里斯汀·休伊特: [00:11:02] 我觉得我很幸运。 所以最初的那种一开始就被反弹并且让眼科医生不想给我回电话也不想见我,这绝对令人沮丧。 但回想起来,我很感激他打了那个电话,因为这意味着我去了教学学校的医疗中心。 我转介的神经眼科医生相对知名。 我的初级保健医生,当他发现我在看谁时,我发现他实际上去上学并为我的神经眼科医生学习。
[00:11:35] 所以他一直在这个领域。 他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他非常善于确保他遵循一切。 他跟着我三年了。 我回想起来,你知道,他本可以在做了一年干净的核磁共振成像并且在第一年没有进行第二次核磁共振成像之后,他本可以轻松地让我出院,但他没有。
[00:11:53] 当我对他诊断出多发性硬化症时给我的诊断感到不舒服时,你知道,他立即将我送到 MS 诊所并让我接受他们的安排,他们得到了我快点进去所以至少对我来说,我知道我有几年没有得到诊断,但我也知道我当时不符合诊断标准。
[00:12:14] 所以很难给我诊断。 但我的医生都没有放弃。 他们继续监视我,当事情真的发生时,他们都非常迅速地采取行动。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与医疗系统相处的时间比我知道的某些人经历的要容易得多。
GG deFiebre: [00:12:31] 好的。 然后,当你经历这些急性发作时,我知道它们是你可以确定的那两种。 也许更早的那些,你知道,这可能归因于 NMO,但你不确定。 对于您经历过的某种急性发作,您接受了哪些治疗? 您是否接受过类固醇或 IVIG 或血浆置换之类的药物? 如果是这样,他们是否有帮助? 你是如何与你的医生合作提出治疗方案的?
克里斯汀·休伊特: [00:13:03] 所以第一次视力丧失是在 2014 年,神经眼科医生让我服用口服类固醇。 而且我认为这就像一个四到六周的课程,我慢慢地逐渐减少。 在那段时间里,我确实恢复了视力。 它很慢。 但是当我停止类固醇时,我已经完全恢复了视力。 第二次发作,那时,我们一开始并没有给我类固醇,只是因为我们把我送到了水通道蛋白 4 之类的实验室。
[00:13:34] 但是一旦我完成了所有的实验室和一切,我们,我就被送去服用类固醇,这非常简单。 他们派我去做 IVSM – IV solumedrol – 那个特定的时间,我做了三天,然后我做了一个锥度。 再一次,我看到这些改进相对较快。 IVSM 的效果比口服类固醇快得多。
[00:13:56] 我两次口服类固醇都有很多副作用。 所以我不再接受那些了。 但我什至不必真正寻求治疗。 第一次,神经眼科医生立即给我开了口服类固醇。 然后对于第二个,我确实问过,你知道,“我们治疗这种直接发作的计划是什么?” 他们告诉我他们要送我去做 IVSM。 因此,在我的实际耀斑期间,我真的不需要做太多的治疗。
GG deFiebre: [00:14:24] 好的。 在这之后你有没有去康复中心,或者任何类似的职业或物理治疗?
克里斯汀·休伊特: [00:14:32] 在这两种情况下我都不需要任何类型的治疗,实际上甚至从那以后我经历过的发作,它们主要是感觉或视力丧失。 我在移动方面并没有遇到太多问题。
GG deFiebre: [00:14:48] 好的。 那么您目前有哪些残留症状,您如何处理这些症状?
克里斯汀·休伊特: [00:14:55] 所以以我的视力,我有光敏性,我看某些颜色的方式不同。 对于那些我只是对夜间驾驶更加谨慎。 有时我的孩子会感到沮丧,我会告诉他去捡一些东西,告诉他那是粉红色的,而且真的很红。 因此,我们不得不通过他的耐心来解决某些此类问题。
[00:15:17] 我最大的问题是感觉。 所以我身体的左侧从我的腰部开始。 如果我累了,如果我太热或类似的事情,我会感到刺痛,几乎就像我的脸一样,我的脸在睡觉,感觉会有点发红。 大约一年后,在那次袭击之后,我的右腿小腿有一种非常糟糕的烧灼感。
[00:15:44] 所以这是我经常有的另一种感觉,就像突然发作一样,那种感觉就像我的腿后部着火了一样,我的腿变得很重。 所以我不能做很多体力活动。 我尽量不把自己逼得太紧,因为我确实开始感觉到我的腿有问题。
[00:16:03] 当我买房子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把房子定在哪里,因为我在黑暗中看不见。 所以就像正常人的视力最终会适应黑暗而我的则不然。 所以我们在房子里安装了动作激活的夜灯。 这样一来,当我走进一个房间时就不会感到不知所措,但我至少有一些光线,这样我就可以在黑暗中穿过房子,如果我在半夜或类似的情况下起床。
[00:16:25] 但是,那些是我的主要残留症状。 当然还有正常的疲劳之类的。
GG deFiebre: [00:16:32] 好的。 是的。 好吧,然后运动传感器亮起,这听起来也是个好主意。
[00:16:37] 所以,你知道,我们谈了一些关于急性治疗的问题。 所以我了解你,你确实在发病期间接受了类固醇。 但是您目前是否正在接受任何长期预防性治疗? 如果你是,哪些? 或者,您知道,您是否一直在更换治疗方法?
克里斯汀·休伊特: [00:16:54] 所以在我 2017 年发作后,当我得到正式诊断时,我们决定让我服用 Rituxan。 我们讲到CellCept和Imuran是当时另外两个大的。 但是因为我的水通道蛋白 4 呈阴性并且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虽然我的成像看起来非常 NMO 特异性,但它总是有可能是 MS。 我们认为 Rituxan 可能是最佳选择,因为它可用于治疗其中任何一种。 所以这就是最有意义的一种。 我还喜欢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不必记得吃药,因为我从不记得吃药。
[00:17:30] 我从 2017 年 2018 月开始服用它。我们没有改变我的实际处方,但我们改变了频率。 所以当我在 XNUMX 年开始在我的腿上突然发作时,我们拍了几张照片。 我们在核磁共振成像中发现的是,我仍然有病变。 它们没有增强,它们不一定引起症状,但仍然有一些活动。
[00:17:55] 然后今年 2017 月,我的右腿又开始有些沉重,但从我的臀部开始越来越重。 所以我们决定让我仍然有一些活动发生,即使它没有增强,然后有自 XNUMX 年开始以来我经历过的那种爆发,因为我也有过,他们发现了一个小点我大脑中的白质。
[00:18:21] 那是在控制记忆的区域附近。 所以我有一段时间有一些短期记忆问题。 因此,正因为如此,我们决定将 ituxan 从每六个月更改为每五个月,我刚刚在去年夏天开始进行这种调整。 所以希望也许增加的频率将有助于防止我看到的那些小复发。 如果没有,我们将开始就可能改变他们的药物进行对话。
GG deFiebre: [00:18:49] 好的。 然后,你知道,我们确实谈到了你的旧病复发。 您是如何认识到自己正在再次发作,而不是只是症状恶化? 我知道你说过有时候如果你做的太多或者天气太热,你的症状可能会恶化。
[00:19:05] 你如何尝试区分复发和症状恶化?
克里斯汀·休伊特: [00:19:12] 所以对我来说,我的复发与之前的任何一次发作都非常不同。 所以我的第一次攻击与我的视力有关。 我的第二次发作与我身体左侧的那种刺痛麻木感有关。 在那之后的一个特别是我小腿区域的右腿。 然后我真正真正注意到的下一个是去年我腿上的那个。 所以它们都是非常不同的感觉。 他们是非常不同的感觉,我想你可以说。 因此,由于它影响了我身体的不同部位,我知道它是某种东西。
[00:19:54] 我也是,当我第一次被诊断时,我对我的医生很感激的一件事是她让我坐下来告诉我,“这就是你要做的,你知道,如果你醒来有一天早上,你失明了,这就是你所做的。 如果你有一天早上醒来,摔倒了,然后瘫痪了,这就是你所做的。”
[00:20:12] 因此,我一直与她进行非常开放的交流,而且我总是对我应该做什么有一个计划。 所以在每一种情况下,我都能拿起电话,给她的办公室打电话说,“嘿,这些是我正在经历的症状。” 然后他们给了我下一步。 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派我去做核磁共振成像,在某些情况下,比如现在有 COVID 和其他一切,他们实际上没有派我去做最近一次袭击的核磁共振成像。 他们实际上继续前进,直接让我服用类固醇。 所以,值得庆幸的是,每当我出现一些奇怪的症状时,我就可以打电话给医生,让她告诉我。 有时她告诉我这可能无关紧要。
[00:20:50] 我有一些内耳和一些平衡问题,她说,“是的,那可能不是 NMO。 去你的初级保健机构,看看你是否有耳部感染。” 结果证明它与过敏和类似的事情有关。 所以如果我有什么感觉有点不对劲,我总是会和办公室联系。
[00:21:05] GG deFiebre: [00:21:05] 好的。 所以非常感谢你带我走过,你知道,你在诊断和治疗方面的经验,以及你的旅程,直到现在。 但是,如果您对诊断有任何与此相关的恐惧或担忧,您是否介意谈谈与 NMOSD 一起生活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
克里斯汀·休伊特: [00:21:25] 所以我认为至少就我而言,对我来说最困难的事情就是疲劳。 特别是最近,我是其中的一员。 我以前的很多次发作……我被诊断出有刺痛/麻木感的那一次,我正处于我职业生涯中最大的项目中,我们正在“周末直播”,而我的手臂上装有静脉注射器.
[00:21:47] 所以我带着静脉注射在办公室里跑来跑去。 所以我一直都是那些喜欢把自己逼得太紧的人之一。 所以对我来说,这是我最大的挑战,因为我必须提醒自己后退一步,放慢速度。 我的身体不能像我习惯的那样。
[00:22:03] 我认为就恐惧而言,我认为我的脑后总是害怕我会再次复发,我会发生更糟糕的事情。 有时我觉得自己有点过敏。 你知道,如果我的身体开始发生奇怪的事情,我就会开始质疑,哦不,这是攻击吗?
[00:22:18] 或者,你知道,所以只有一点点恐惧和担忧,你知道,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或者之后会发生什么?
GG deFiebre: [00:22:29] 对。 正确的。 然后,你知道,另一方面,作为与 NMO 一起生活的人,你有什么希望?
克里斯汀·休伊特: [00:22:37] 所以我充满希望。 我的意思是,显然对于那些水通道蛋白 4 呈阳性的人来说,在过去 18 个月中我们在药物和研究方面取得了如此大的进步。 即使只是对 MOG 进行商业化测试也是另一项进步。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有很多希望。 你知道,希望他们能为我们这些血清阴性的人找到另一种抗体,这将有助于,你知道,对我们形成更好的治疗方法。 希望,你知道,我们继续通过我们长期拥有的药物和选择取得进步。
[00:23:11] 但我认为,从我三年多前的初步诊断开始,甚至在此之前,有一种不知道自己拥有什么的不确定状态,这真是太棒了在过去的几年里突飞猛进。 因此,这肯定会让您对未来充满希望。 但在那段时间里活着并见证所有这些进步也真的很酷。
GG deFiebre: [00:23:35] 是的,当然。 那么关于治疗 NMO 患者,您有什么希望医疗专业人员知道的吗?
克里斯汀·休伊特: [00:23:45] 我不知道。 所以我的核心医生团队很棒,我非常感谢他们。 但有时当我去其他地方的提供者那里时,我会得到两种不同的反应。 我有一组不想碰我的医生。 你知道,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都希望由神经病学团队负责,他们希望确保一切顺利。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我希望他们知道,就像我仍然是一个正常人一样。 我还是一个普通的病人。 就像我希望你那样对待我。 然后我有医生,当他们发现我有 NMO 时,我就变成了他们想要学习、谈论和研究的独角兽。
[00:24:15] 我看到一位耳鼻喉科患者在见到我前两天阅读了纽约时报关于 NMO 的文章。 他以前从未听说过 NMO,现在他读了一篇纽约时报的文章,他的办公室里坐着一位病人。 当他的护士稍后去打印我的,我的东西时,她无法理解它,因为他做了关于 NMO 和纽约时报文章的笔记,而不是关于我为什么在那里的笔记。
[00:24:36] 所以我认为在这两种情况下,我认为这是关于意识到,你知道,我还有其他问题。 我仍然,你知道,NMO 不是我。 它没有定义我。 这么理解我,我仍然是一个人,除了 NMO 之外还有一些事情要看。 因此,我认为这是我对那些不习惯看到患有罕见疾病的人的医疗专业人员的最大反馈。
GG deFiebre: [00:25:01] 对,对。 然后是您希望您的朋友和家人了解 NMOSD 的任何事情。
克里斯汀·休伊特: [00:25:09] 你知道最近,我觉得他们对待我的方式好像我没那么能干。 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这又回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需要记住我并不总是那么有能力。 但是我们要搬出一栋办公楼,我觉得和我一起工作的那个人一直在努力收拾所有的箱子,这样我就不必收拾箱子了,我可以收拾箱子。
[00:25:30] 所以有时我只是希望他们……我很欣赏他们这样想。 但我也有点希望他们不会因此而区别对待我。 所以我认为这将是我的家人和朋友的唯一一件事。
GG deFiebre: [00:25:45] 是的,当然。 那么,你知道吗,你如何向其他人解释你的诊断或 NMO? 你知道,无论是同事、朋友还是家人,你如何解释这种疾病如何影响你的生活,你知道吗?
克里斯汀·休伊特: [00:26:01] 所以我实际上对大多数人都很开放。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我曾经就 NMO 如何影响我的生活进行过必然的对话。 但我一直很开放,我通常使用 MS,因为大多数人都知道 MS 是什么。
[00:26:17] 所以我有点用它来解释 NMO 是什么。 所以我会,你知道,和他们谈谈我是如何患上脑损伤和脊椎损伤之类的。 我们确实谈论药物。 有了 COVID 和整个关于免疫功能低下的谈话,我的药物治疗变得比以前更像是一场谈话。
[00:26:38] 现在,如果我出现在办公室,我会受到盘问。 你为什么在这? 你不应该在这里。 但我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我的家人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给予,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解释,但不一定是超级深入的解释。 从我的家人那里,我得到了两种反应之一,这有点类似于同事的反应。
[00:26:58] 我要么有家人,现在他们超级担心,他们非常担心,这是一种恐惧。 或者他们因此而对我有所不同。 所以我试着把它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而不是过多的细节,因为我不想让每个人都担心,我不想让他们认为我,我不一定有能力所有这些,我以前的事情。
GG deFiebre: [00:27:18] 对。 正确的。 然后,你知道吗,你还有什么我没有问过的,你最后的想法或其他任何你想提的,关于你作为 NMO 的人生活的经历吗?
克里斯汀·休伊特: [00:27:32] 不一定。 我认为我唯一想添加到关于家庭的对话中的另一件事。 所以我是单亲妈妈。 当我第一次发作时,我的儿子才三岁。 所以他是在我生病的情况下长大的。 当我与其他患者和类似的事情交谈时,我知道对于很多父母来说,他们没有,你知道,有时他们觉得他们的孩子有点吃亏,或者他们不像能够像父母一样好。 所以我肯定有一些限制。 肯定有几天,你知道,我希望我是,你知道,和他一起做活动,但我躺在床上,因为我感觉不舒服。
[00:28:08] 但我的医生甚至评论的一件事是,我让他成为我旅程中的积极部分。 当我们向他解释 NMO 时,因为他太小了,我们告诉他我脑子里有嘘声。 我回家时手臂上插着一根静脉导管,我们会讨论这个。
[00:28:28] 所以对我来说,我认为这段旅程中最艰难的部分之一就是他与此一起成长,并与所有这些事情一起为人父母。 但我非常感激,因为现在他已经对放血是如何进行的非常感兴趣了? 他想看看他们是如何抽血的,他想看看核磁共振成像,他想做所有这些事情。
[00:28:48] 因此,对于拥有 NMO 的父母来说,与您的孩子进行公开对话是一回事,因为他们对您正在经历的事情有了更多的了解,所以您不会当你感觉不舒服时,你不必感到内疚。 而且,我认为是,我认为这让他大开眼界,看到了在他这个年纪,他以前可能不会经历过的事情。
[00:29:09] 我喜欢看着他的兴趣,他的成长,想看看成像和医学的东西等等。
GG deFiebre: [00:29:15]哦,是的。 不,那是,那是,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观点。 非常感谢您今天抽出时间。 真的很感激。 并分享您的故事。 你知道,我知道有时候谈论起来可能很困难,但你知道,我们真的很高兴听到你的故事,并了解更多关于与 NMO 一起生活的感觉。 所以谢谢。
克里斯汀·休伊特: [00:29:34] 非常感谢。
收听并订阅
播客
下载MP3
下载成绩单